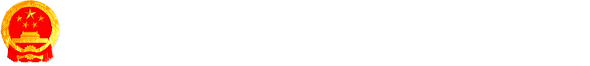“楚豫连疆一轨通,车停山下我徂东。拨云直上鸡公顶,丘壑楼台燣眼中。”
鸡公山地处桐柏山和大别山之间,上世纪80年代,面积27平方公方公里,现扩至287平方公里。平均海拔700米左右,自古为南北要冲,山系两侧有古驿道通过;清末修建的卢汉铁路沿西侧山脚下的李家寨、武胜关通过;清末修建的卢汉铁路沿写测山脚下的李家寨、武胜关经过,使西方传教士发现了鸡公山蕴含的巨大避暑资源,遂购地建房,大肆宣扬,鸡公山始名扬天下。到1936年,鸡公山共计有美、英、法、德、俄、日等23国别墅368幢,夏季高峰时居山西人达2200余人。昔日寂静的山巅变成一座惬意、繁华的休闲别墅山城,鸡公山因而成为国内与庐山、北戴河、莫干山齐名的四大避暑胜地之一。
经历百年的沧桑岁月洗礼,昔日的筚路蓝缕早已成为过去,昨日的商场教会也已物是人非,登山古道熙熙攘攘不再,鸡公山历史文化遗存中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具有域外风格的各幢建筑群落,虽经百年的风霜雨露和社会变迁仍如一颗颗明珠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仿佛在述说着那古老的辉煌。然而。除却散布于山巅的西方各式别墅、教会、学校建筑以外,天街、避暑山庄、佛寺道观及昔日的登山古道在鸡公山近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当中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内陆租界的劳役服务区——天街
“本山之街市,盖因山路崎岖,不得不遂地势而建市街也。已笼子口以南曰南街,北曰北街,均各沿溪谷(西为西沟,东为鸡公沟)而成。由南街向南行,沿鸡公沟一带之地,为避暑官地区,南岗之鄂界官地为其终点。由北街向北行,沿西沟一带之为教会区。”(1936年版齐光著《鸡公山指南》)
天街为鸡公山一个特殊的居民集聚区,位于山巅风景区的西北部、临崖而设,宽约3——5,米,包括南街和北街两部分,两节以笼子口为界,南街略呈“S”形,居民多来自湖北,北街则呈”Z”形,居民多来自河南。南街在21世纪初经过改造,两侧建筑已失去历史原貌。北街现今微显萧条,但街衢格局仍在,部分建筑历史风格依旧。
1921年徐珂著《鸡公山指南》指出,早在1908你那”山之衢市不甚盛“,除邮局以外,还有中瀛照相馆、 利呢绒西装店,共和兴洗衣店、理发店等。由外国教会于1925年编印发行的《鸡公山指南》指出:”邮局附近,华人居住区有几家杂货店和其他日用品商店,其货物售价与汉口相当,”这里讲的“邮政附近”指的就是南街。
天街形成于20世纪初,由于鸡公山别墅群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山巅常住人口铺的增加也需要和周围具备提供相应的生活必需品保障服务的能力,这样一个集聚居和商业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商业街在登山古道入口处——笼子口就诞生了。之所以在此选址,其原因有三:一位于山巅入口处,方便劳力集散和建设物资运输;而方便生活必需品集散,辐射整个山城;三沿笼子口两侧临崖而设曲蜿蜒,地势“低洼”,位置“偏僻”。不占用有限的可建设土地资源。
鸡公山北街建筑依地势并排错落而建,砖块砌体夹街对峙,多为两层,珩架结构。机瓦或步瓦屋面,檐口下普遍设有铁皮水槽,将雨水沿落水口和落水管贴墙壁注向地面;门窗洞口或用石条过木,或用砖券(平拱或坦拱);部分建筑砖壁外辐射砖柱,具有很强的中国近代风格。鸡公山天街布局密集,建筑促狭,与官地建筑反差强烈,是中国近代开放区社会底层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中国近代开放区衢市建筑格局的代表。
二、中外文化对抗的见证——避暑山庄
鸡公山避暑山庄又称“河南新店避暑山庄”,位于鸡公山西北侧马鞍山一带,“距北街六里,距新店十二里”,始建于1919年,由时任京汉铁路漯河至汉口段长易怀远等人发起创建。是在鸡公山避暑山城过程中全部由中国人建造的一处近代避暑园林区。
鸡公山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人李立生购地建房始,西人纷至仿效,两年间建房总数达27处之多,并呈迅猛发展势头,鸡公山深居内陆,非开 通商之地,西人在山所购地产于条约无据,严重损害了清政府主权。“光绪三十四年,西人扩地达九百二十三亩,鄂豫疆史乃奏请收回地方主权......除服务教会之西人所住地方五百亩外,凡西商所住之区,均准有我国备价收回,定为避暑官地。未收回者,定为教会区,余为鄂、豫两省之森林区,今仍之”(1936年版《鸡公山指南》)。鄂豫两省官员经过交涉,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会同英驻汉口总领事馆签署《鸡公山收回基地房屋另议租屋避暑章程十条》,收回西人自建之房屋。然而,西人以传教公产之名强划教会区,仍占用五百亩。,实际上成为内陆鸡公山的“公共租界”。
1936年版《鸡公山指南》:“教会区在昔年除出入山大道,因通必经之路,准许华人行走外,其他各街巷,均不许华人涉足。”官地区在收回后实际仍有西人及机构使用并控制,华人不能在此居住,只有在此外的森林区才是中国人的可建可居之地。“本山避暑人士,在民国十五年以前,凡教会区与避暑官地区,在未完全收回时,仅准西人居住,吴子玉当权时代,靳云鹗欲于避暑管地区建屋避暑,屡商之西人,均无效果,后乃侍其权威,强建其颐庐于森林区及避暑官地区之间”。在吴佩孚当政时期,即使是北洋政府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欲在官地区边缘兴建别墅都与西人多次协商未果,最后强建颐庐,一般中国官僚和商人更不在话下。
鸡公山避暑山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民国官僚、军阀和商人集资创建。初创时始有股东6人,1921-1925年,山庄进入建设高期拥有股东40余人,计划筹建48组别墅,实际竣工只有8组别墅。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因忙于战事,无力暇顾,山庄随即荒废解体。
1936年版《鸡公山指南》述避暑山庄:“庄内有一所名曰天福宫......有学校一处......退思亭、颐心园,均为庄中有数之建筑;“庄中共计八户,建筑悉以西式,长桥曲路,红树白云,四时时光,各具奇致;而听涛亭独出其北,观瀑亭辟居其东,峰回路转,形式之胜,实无与俦!”
《现阶段鸡公山》(1948年)述避暑山庄环境:夫出鸡公山外,自成一区......其西北隔西有学校/有民房,随仅八户,而别成村落,对溪而居,殊饶风味。加上溪上长桥如龙,水绿倒映,世外桃源,当不出斯也”。
鸡公山避暑山庄是中国军阀、官僚、士大夫阶层在近代形势下把传统实景园林与近现代建筑结合的典范,是近代社会上层人士对中国传统园林建设的创新与发展,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与外部入侵势力对抗的历史见证。今鸡公山避暑山庄保存有箫家大楼、卧虎楼王澍生别墅、翠云楼、另有公共建筑公事房、耸青阁和环翠楼,以及山庄学校。各建筑依山就势,布局舒朗,造型风格比照西方别墅样式,但在整体布局及细部建造手法中隐约透出传统园林文化的某些影响。
三、传统文化的雨露滋润——佛寺道观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佛寺道观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俗语有“世间好语书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说。世俗观念的“万物有灵“与宗教倡导的“物我同化”在名山大川中找到了融合的道场和身心修炼升华的阶梯。鸡公山因开发较晚,居民构成中西人较多,传统的道教、佛教文化也别具特色。
青峰寺,1921年《鸡公山指南》:“山之建筑,自西人庐舍及阛阓外,有青峰祠,有教堂,有美国人所设之学校......”刘景向的《鸡公山竹枝词》中有“叠石玲珑似酒垆,山巅悄锯草芜芜,游人探得青峰寺,也算骊龙颔下珠”之句。刘先生又讲:青峰寺。又称青峰祠,“规模小如垆灶,叠石为之,兀踞鸡公山西面。颔珠之喻地位云尔”。鸡公山在《水经注》中称鸡翅山,明代称为鸡头山。既以山名,则鸡必灵。中国的道教为多神教,民间在鸡公头下叠石为坛,进行祭拜,也是纯铜道教祭拜的一种常见方式。徐柯与刘景向先生均在文献中对小小的青峰祠有所提及,可见其在鸡公山传统文化中的影响之深。
灵化寺,史上又称灵化山,,1936年版《鸡公山指南》:“灵化山在鸡公峰下,约二里许,地据鸡公山避暑官地之外,初为宦途失意人苏斐然氏以神道之力,独手创建,而自成一道教活动之区,此山之得名,即为苏式所命出,信徒众多,闻达官显宦,亦不乏其弟子”,苏道士失踪后,道观由其妻主持,香火日衰。灵化山入口处有石牌坊一座,正面楹联:“归元之路,入圣之门”,背面书“天中蓬壶,室外桃园”。道观内“建屋三栋,朝男背北,前为园圃,......园旁为为第二静室与第一静室,均在平台之下,台上为禅堂及待客室,室中供一篆文”灵“字,绝无塑像木偶之属,亦一别开生面之庙宇也,”室内陈设的匾额及对联均出自名家之手。
今“灵化寺”名称及山门均为后人衍化并增建,实为史上一道教福地。据何先生考证,苏斐然本为心海义士,后追随孙中山讨袁护国。蒋介石“四 一二”事变后于1929年入鸡公山创立“灵道学社”。从文献记载可知,灵化本无“寺”这一组织机构,然因灵道文化影响之深,自发信徒聚众为多,“寺”山也就自然同体,后人默认灵化山为“灵化寺”也就顺理成章了。
天福宫 1936年版的《鸡公山指南》:“佛教寺院在避暑山庄建有天福宫一所,为在家和尚所主持,冬去夏来,平时仅有人焚香礼拜,居民虽大部分崇奉斯教,信徒不谙经典,皆为拜灶王,供土地之多神教徒儿”。“庄内有庙一所曰天福宫,中供佛像数十尊,金身辉耀,神态毕肖”。佛教岁伟外来宗教,但在漫长的历史传播发展过程中早已经完成了本土化,佛教倡导的禅法修行理论对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有深厚的影响。天福宫虽未寺院,但为居家和尚所主持,佛像/教义虽在,组织结构未健全,修行方式自然显得不那么“专业”。《河南新店避暑山庄庚申记 奉六道人总批评》:“易子靖戎,好山、好佛、好道、好友......”。既为“好”。表明“业余”的倾向性很强,“不谙经典”也情有可原,同时也显示了时下中国士大夫“出世入世”观念两面性。其后入住 山庄的箫耀南亦信佛,天福宫即为箫所建。
活佛寺 1948年版《现阶段鸡公山》:“出南岗下约三里许,沿山道直下,至途中,忽然发现山谷中有双旗杆竖立者,即活佛寺也。......寺内供奉济公及其他神像,房屋矮小而设备精致,亦司可取”。相传活佛寺为湖北人英富商厨师尹寿耐于1932年所建,因尹妻及二子相继病亡,尹认为前世有过,遂有今生之难,随积毕生之力修建寺庙,以求安宁。
鸡公山本为一座风景旖旎的荒山,经二十世纪初期西人的开发宣传,遂成一座繁华的季节性山城,这其中西人的主导作用易见。在“十里风飘九国旗”的环境下。国人在山的存在反而有点“反客为主”的情形,这显然是国力衰落影响所致。与“东岭西浴人络绎,喃喃都颂耶和华”相比,古老的中华文化内敛/柔韧,中华传统宗教在强调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下注重自修,道家注重修身,佛家注重修性,其自修的过程不事张扬,低调、内敛,因此佛寺道场多远离繁华,以利于身心与自然的融合,鸡公山传统宗教文化如山间涓涓清泉汩汩滔滔,滋润无声。
四、华丽山城的彩色丝带——登山古道
“丹崖白石响丁丁,石破崖崩天亦惊,不为金牛开蜀道,恺崇楼阁斗峥嵘。”鸡公山山势陡峭,工程浩大,建设周期漫长,在鸡公山的开发建设中,登山古道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8年版的《现阶段鸡公山 鸡公山游览概况》:“车站距鸡公山避暑地界十二华里,大道有二:其一由寨里徐棚经过,于龙子口入山。其一由避暑山庄经过于北岗入山。普通多循前径,以其路较广坦,山坡陡峭处即设有石阶上登较易。”
古道起自卢汉铁路东侧15米的山坡(系建有花岗岩石柱门),龙子口道路曲展伸展,宽约2——3米,陡峭处以条石为阶,共有1221个台阶。时而林森,茂密、峰回路转,时而昂首高登、絮絮怦怦,时而豁然阔步,直通幽处,沿途有天梯、牛儿寨、二道门、甘泉、怪石等,路旁有多处古人提字如“青分楚豫,气压嵩衡”“陡崖石”等,昭示着古道的人文气息,更有庭栏,石物、石凳凳侯人小憩。
“聊将藤椅作肩舆,八足称风力有馀二道门高弹指过,尘劳暂息 长嘘”。新店车站依偎于鸡公山脚下,距山巅十余里,避暑消夏上山只有古道,西人显贵为免除跋涉之苦多乘“肩舆”代步,因而也催生了一大批靠此谋生的产业大军,据刘景象先生记载即不下数百人。
1963年盘山公路开通,登山古道逐渐荒废。旺季时节虽有游人登临,也与历史上的熙熙攘攘形成强烈对比。然而对于近代山巅之城,十里古道犹如一系彩带。是维系避暑山城繁荣的神经线与血脉流,无视或废弃了古道,作为避暑之地的这颗明珠就成了一座漂浮在历史天空中的文化阁楼。
五 结语
鸡公山是近代开发的一座避暑山城,鸡公山是一座近代万国建筑文化荟萃的山城,鸡公山是一座饱含中外历史文化信息的古城;鸡公山又是一座见证了中国外交发展历史的山城,亲历了中西方民族及文化之间的仇隙与友谊、对抗与合作、交流与融合。
鸡公山人文自然同呈,历史文化信息丰富。在众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当中,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旺旺被边缘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劳众对鸡公山开发的贡献往往不被重视。“高峰揽尽到山根,华屋相邻有筚门。眼底枯荣堪领悟,大观园里稻香村。”刘景象的诗句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华人生活与鸡公山西人显贵的巨大落差,是对当时的社会的讨伐和鞭挞。